
最是仓皇辞庙日,教坊犹奏别离歌(3首亡国君王的诗词)

公元975年的初冬,是北宋开宝八年,也是南唐建国的第38年。
金陵已经被北宋大军围困了十个月,城中米粮匮乏,死者不可胜数,使臣徐铉再一次站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面前。
上一次,他极力夸赞后主李煜的才华与德行,还当面诵读了李煜的诗歌,却被赵匡胤讥刺为“寒士语”。
这一次,他表达了南唐的恭顺,恳求能放过南唐国一马,暂时保全“一邦之命”。赵匡胤却向他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:
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!

在大宋开国之初,赵匡胤夺走后周柴家的山河后,“识时务”的李煜便主动派人到东京,请求自削尊号,改称“江南国主”,并卑微地让赵匡胤直称其姓名。
后来,在大宋陆续收割其他割据势力时,南唐一直站在大宋的背后摇旗呐喊。但屈尊事宋并没有带来多少年的和平,南唐终究难免一亡。
在江南湿冷萧条的十二月,金陵失守,李煜肉袒出降,南唐灭亡。
被带往东京后,李煜用一阕《破阵子》,记录了当时的困窘狼狈:
四十年来家国,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,玉树琼枝作烟萝,几曾识干戈?
一旦归为臣虏,沈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,教坊犹奏别离歌,垂泪对宫娥。

南唐开国三十八年,版图共有三十五州,方圆三千里,一度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国家。
历经一帝二主,建立了高大雄伟的宫殿,危楼高阁,栖凤盘龙;种下了珍贵茂盛的草木,鲜花遍地,藤萝缠蔓。
据宋人笔记记载,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,以绿钿刷隔眼,糊以红罗,外种梅花;梁栋、窗壁、柱栱、阶砌等都作隔筩,密插杂花,可见其豪奢。
江南温软的雨丝风片,绮丽的烟波画船,相伴着骚人词客、粉黛娇娥,哪里曾见过战争的铁血与惨烈呢?
而一朝降而被俘,忍辱含垢、苟且偷生,怎不令本就多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呢?

沈约晚年遭皇帝猜忌,多次辞官却不被准许,只能日日生活在忧惧之中,以至日渐消瘦。
潘安才华出众却遭人嫉恨,被排挤出朝廷,又不幸爱妻亡故,32岁便已两鬓斑白。
看一看眼前逼仄的幽禁之地,想一想仓皇地辞别宗庙时,宫中的乐工吹奏起别离的歌曲,李煜的心中既有对未来的惶恐不安,又有对祖宗的羞惭愧恨,更有对故国的留恋不舍,却无处可诉说,只能对着宫女默默流泪。
由极盛转至极衰,由极乐转至极哀,转得不露痕迹,却又重于千钧。一个亡国之君的内心独白,是何等的惨怛沉痛。

有一个传说,说宋徽宗赵佶是李煜的转世,是为了灭亡大宋而来。
传说终归是无稽之谈,但赵佶确实是一位风雅帝王了。虽然写词远逊于李煜,但书画上的成就却颇高。
靖康之变后, 赵佶、赵桓与数万贵族、宫人等被掳掠,一路北上被押送到金国。
途中,路过燕山府外的驿亭,赵佶悲从中来,写下了《燕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。词中,他自比为“易得凋零,更多少、无情风雨”的杏花,悲叹“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”。
他怜惜那风雨中飘零的杏花,在凄凉的院落中自开自落,更怜惜自己在战乱中零落,流徙至千里之外,且问且叹,如泣如诉。

不过严格说来,北宋灭亡时,皇位上坐的是宋钦宗赵桓。
赵桓是赵佶的长子,16岁便被立为太子。十年后,金国大军压境,父皇匆忙禅位,给天下换了个皇帝,也试图把亡国的黑锅强行甩到了他头上。
实事求是地讲,赵恒上位只有一年,且匆忙禅位间权力并未及时交接,许多朝中大事依然由赵佶和旧臣决策。
如果赵恒是唐肃宗李亨那样,趁唐玄宗亡命成都,就趁机在外称帝的铁血帝王,或许北宋尚有一线生机。
可惜,据史料记载,赵桓为人优柔寡断、反复无常,不仅懦弱无能,而且挺喜欢听信奸臣的谗言。短短一年多的执政生涯中,走马灯似地提升与罢免了二十六名宰执大臣。北宋的倾颓,注定无力回天。

若提到北宋的亡国诗词,当属父子俩在北行途中唱和的两首《眼儿媚》。
《宣和遗事》中记叙北行的路途之上,“草莽萧索,悲风四起,黄沙白露,日出尚烟雾,动经五七里无人迹,时但见牧羊儿往来”。
一日,众人在林中夜宿,月色微明,金人笛声呜咽,赵佶写下了这首词:
玉京曾忆旧繁华,万里帝王家。琼林玉殿,朝喧弦管,暮列笙琶。
花城人去今萧索,春梦绕胡沙。家山何处,忍听羌笛,吹彻梅花!
写罢,他让儿子和诗一首,赵桓依照原韵答词一首:
宸传三百旧京华。仁孝自名家。一旦奸邪,倾天拆地,忍听琵琶。
如今在外多萧索,迤逦近胡沙。家邦万里,伶仃父子,向晓霜花。

很明显便能读出赵桓的词作水平比其父更低了,这也与史书上记载他不爱声技音乐等“风雅”行为相符。
但赵佶的所有诗文中,只一味柔弱哀戚,自怜自伤。赵桓于惶恐悲哀之外,尚有几分不甘,以至于之后问出“我今父子在穹庐,壮士忠臣何处”之语。
忠臣何处?所有的亡国之君都觉得该有忠臣来救自己于水火,但哪一个国家的毁灭,与国君的行为无关呢?
南唐力主变法却被逼自杀的潘佑,金陵城破力战而死的守将和自缢殉国的陈乔,金军南侵时竭力反对迁都却遭贬斥的主战派“擎天一柱”李纲,二帝被俘时豁出性命维护他们尊严的李若水、张叔夜等忠臣良将,又有什么好下场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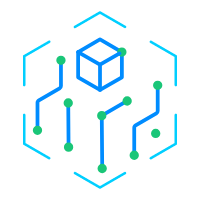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收款码
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
支付宝收款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