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谁知枕上情无限,物是人非古到今(四首世事变迁诗词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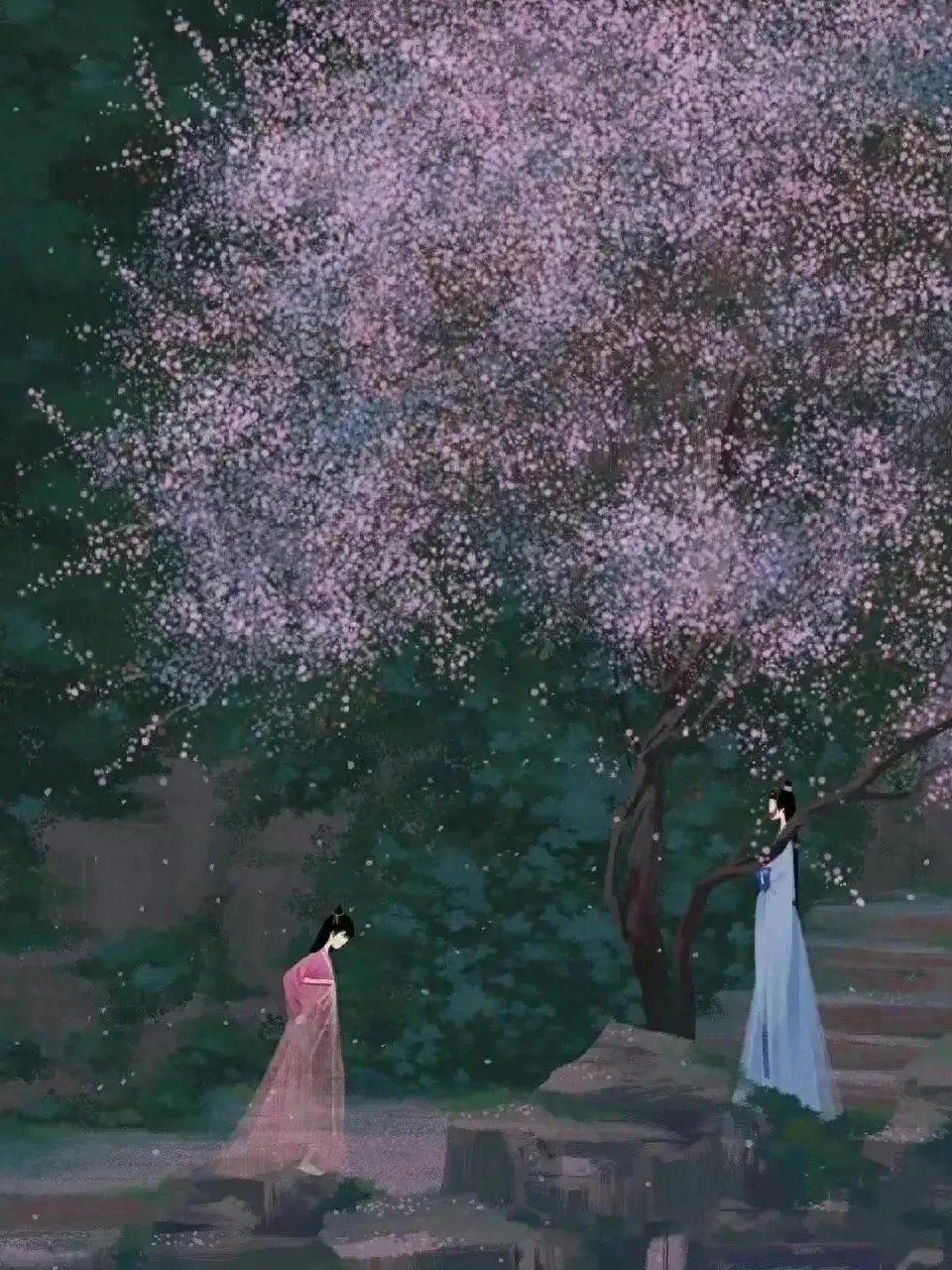
回忆总是在物是人非的时候熠熠生辉,而真正接受了物是人非,也就明白人生不过尔尔。
青春里的错过,就像《匆匆那年》,还设想如果再见红眼还是红脸,要互相亏欠要藕断丝连。
等到故地重游,来到你曾经的城市,走过你来时的路,还期待你突然出现,说句《好久不见》。
《十年》之后,我们终于明白,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,也为别人而流,只剩回忆留在原地。
待到人到中年,笔头风月时时过,眼底儿曹渐渐多。有人问我事如何,人海阔,无日不风波。
如果要形容一段物是人非的感情,我想这或许是大概的心理轨迹,总有一天会被时间抚平。
可终究我只是我,代表不了所有人。总有一些人愿意活在过去,从刹那间获取永恒的记忆。
它或许是故人旧梦,或许是故地乡土,或许是故国往事,纵使物是人非,也要不断地缅怀。
于是在这物是人非的慨叹里,我们又相信了有些东西不会变,有些人的深情可贯穿生命始终。
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。试看这春波荡漾里,有多少春如旧与人空瘦。

1
离别家乡岁月多,近来人事半消磨。
惟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
—唐·贺知章《回乡偶书二首·其二》
当86岁的贺知章辞官还乡,回到阔别已久的越州,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世事变迁。
从36岁状元及第离乡到86岁官居三品归来,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的长度,而人生不过百年。
尤其能如贺知章这般富贵寿考之人少之又少,为了这次回乡,唐玄宗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荣耀。
玄宗亲自赠诗送行,皇太子也率百官饯行。可纵使如此风光,也没有抚平贺知章的浓浓乡愁。
待他荣归故里还没来得及近乡情怯,就被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而重重一击。
本来他以为即使少小离家耋耄回,可乡音未改或许就能掩盖他游子归来的身份,不显得突兀。
没想到,村头儿童的反应让他惊觉自己已成了他们眼里的他乡之人,百感交集已是不言而喻。
而暂时隐去不表的无限感慨,等他到了镜湖边上终于汹涌而至,近来人事半消磨,了无痕迹。
五十年世事变迁,半世纪生死悲欢,贺知章落叶归根后,体验到物是人非的巨大心理落差。
这种落差,纵使皇恩浩荡和富贵寿考也无法弥合,因为那些消失的故人与旧事永远无法重现。
终究,只有门前的镜湖春水依然绿波荡漾,随着春风涌起的层层涟漪,还是当初最美模样。

2
红笺小字,说尽平生意。
鸿雁在云鱼在水,惆怅此情难寄。
斜阳独倚西楼,遥山恰对帘钩。
人面不知何处,绿波依旧东流。
—宋·晏殊《清平乐·红笺小字》
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每当提及物是人非的爱恋,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是绕不开的经典,百读不厌又念念不忘。
因为大部分人都曾经历爱而不得的情感,有的甚至只是默默暗恋,属于一个人的地老天荒。
晏殊笔下的主人公,也正在承受爱而不得的思念与折磨,恨不得用红笺小字,诉尽浓浓爱意。
可纵使写得密密麻麻,说得缠缠绵绵,这份深情也无法通过鸿雁传书、鱼传尺素来传达倾诉。
因为人面不知何处去,山长水阔无寻处。如此音尘断绝,纵使爱如潮水,也只能吞噬自己。
就像此刻独倚西楼,看着残阳一点点下沉,远处青山正对窗内帘钩,而所爱之人更在青山外。
这份惆怅难解的思念,越是登高远望,越是挥之不去,就像窗外碧水悠悠东流,无休又无止。
不只永无止尽,而且还不断地提醒着主人公,春波依旧此情依旧,可玉人倩影早已不复东流。
最终,崔护是在桃花灼灼里缅怀一见钟情的爱恋,而晏殊则在绿波依旧里惆怅相思难相见。
诉说思念的参照物变了,可物是人非的感慨并无不同,同时同地同景,却再也无法携手同行。

3
城上斜阳画角哀,沈园非复旧池台。
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—宋·陆游《沈园二首·其一》
陆游笔下的绿波依旧,属于曾经沧海的唐婉,比崔护与晏殊的物是人非多了沧桑与沉重。
崔护与女子,属于萍水相逢即擦肩而过,故事开头刚刚写好,还未填充过程,即迎来结局。
它更像年少欢喜,不知情之所起就无疾而终,只能在回忆时熠熠生辉,缅怀青春也缅怀自己。
晏殊的情感更为含蓄,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头又如何收尾,只留给后人他被思念折磨的模样。
这些情感固然美好,可没有经历过柴米油盐和阴阳相隔的沉淀,不知这种深情能延续几何。
而陆游对唐婉的思念,从二十岁喜结连理到八十五岁寿终正寝,几乎耗尽了一生,至死难忘。
此诗写于陆游75岁重游沈园之时,唐婉已梦断香消四十四载,可陆放翁依然情难断意难平。
他除了悼念,更夹杂着当初妥协于母亲棒打鸳鸯的无奈悔恨,别人爱而不得,他却得而复失。
这种落差,或许比从未得到更令人难以承受。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,并非虚言。
而此刻桥下绿波依旧荡漾,可曾经那个翩若惊鸿的绰约女子再也无法倒映在这一池春水之上。
河桥摇曳伤心绿,陆游余生无法再走出。

4
淮左名都,竹西佳处,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,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窥江去后,废池乔木,犹厌言兵。渐黄昏,清角吹寒,都在空城。
杜郎俊赏,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,青楼梦好,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,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,年年知为谁生?
—宋·姜夔《扬州慢·淮左名都》
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?
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杜牧,回到长安后还对那里的风流旧梦和风流故人念念不忘,写诗寄赠。
可待到金兵南下,22岁的姜夔看到被战火洗劫后的扬州古城,杜牧的这些风流书写也成了物是人非的佐证。
曾经杜牧笔下的春风十里繁华,到如今只剩古木凋零、池台残断,眼前纵有荠麦青青,也难复当初“谁知竹西路,歌吹是扬州”的热闹模样。
彼时是载歌载舞,此刻只有斜阳暮色、寂寞空城和戍角哀鸣,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纷乱恐慌。
这份昔盛今衰的残酷对比,青春正好的姜夔无法承受,他相信就算是杜牧重游此地,也会深感触目惊心,悲哀难平。
杜牧再也无法以风流笔触写出昔日盛景,他曾经怀念的二十四桥明月夜,不见玉人难闻笙箫。
如今只剩冷月无声,碧波依旧,还有桥边红药,风里花开不知谁是主,又在为谁盛放为谁妍。
如此一来,绿波依旧和芍药花开,从眼前实景到杜牧诗情,成了今非昔比的参照物和见证者。
同样哀叹物是人非,一旦从情情爱爱延展到历史长河,这种诗情画意就变得厚重,令人惊醒。

虽然时间不是考验人类情感乃至历史兴衰的唯一因素,可总能过滤一些东西,抚平一些东西。
不管最终是否接受时过境迁里的物是人非,时间总会奔涌向前,而我们也终将逝去。
杜甫曾慨叹李白,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可平凡如我,也只有寂寞身后事了。
物是人非事事休,不如珍惜眼前年年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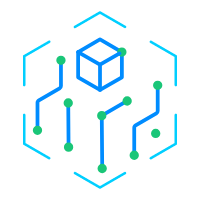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收款码
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
支付宝收款码